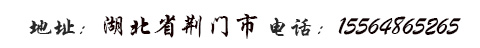猜想十从台州沿海的沧桑,看杭州地理的
|
在前面几篇《杭城地理变迁之猜想》中,笔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、看法,试图对于杭州地理变迁过程中一些无法知晓的谜底,加以解答和证明。 至于这一些观点的形成,也是出于一种机缘巧合。 很大程度上,这些观点,是基于笔者对于自己台州的地理历史变迁的认知、对于杭州地理历史的理解分析,而得出的。 台州和杭州,虽然都属于浙江,但一个是沿海城市,一个是沿江城市,一南一北,相距较远,甚至在气候上也有些不同,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。 然而,在地理成因上,台州的沿海与杭州城区多有相似之处,都是围海造田的人工杰作。 笔者从小生活在台州,后到杭州学习工作,此后也一直生活在杭州。两地都给笔者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,因而常常也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比较。 相比而言,台州沿海地理的演变和形成,要迟得多。所以,对于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,存留下来的地理印记和流传下来的历史的记忆,也会多很多。 基于这一些,笔者产生了一些猜测和想象,并写下了《杭城地理变迁之猜想》一文,后作修改并分篇,在修改前,原文的副标题就是“由台州沿海的百年地理变迁,猜想杭州城区的千年地理变迁”。 一、“长塘河”星罗棋布的启示。 今天如果我们打开卫星地图,可以在台州路桥的沿海一带,看到星罗棋布的河道,其中南北向与海岸线平行(彼此距离大约都是一公里)的众多河道,就是所谓的“长塘河”。 这些“长塘河”是围海造田所遗留下来的,从前人们大致是这样围海造田的:官方组织大规模的劳动力,在远离海岸的海涂上排开,就地取材进行筑堤围垦。其堤坝是直接从边侧取土堆积而成的,开始一般在外侧取土,后期在内侧取土,取土后就会留下沟壑。堤坝外侧随着一次次被浪冲刷,沟壑慢慢不留痕迹。而内侧的沟壑就会形成为河道“塘河”,这就是所谓的“塘”。 而等到这一塘围垦成功后,再围垦下一塘,这样周而复始日积月累,就会形成一座座一条条彼此相隔一定距离的“塘坝”、“塘河”。 几百年来,当地的人们,就这样从一塘、二塘、三塘、……、九塘、十塘,一步步向东海推进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些远离海岸线的“塘坝”逐然失去原有的作用而慢慢湮灭,而“塘河”因为具有交通和灌溉的功能而被不断疏浚而保存下来,就形成了这样一条条长河(“长塘河”)。 笔者家的后院对着的就是这样的“长塘河”,是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地方。 到杭州工作后,一开始居住的地方是望江门外秋涛路边,秋涛路肯定也是塘坝遗址。 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,也亲眼目睹过,秋涛路改造期间,建筑工人下挖下水道时,裸露出一整排长条石叠砌成的、如同城墙一样的堤坝,而且其西侧也是河道。 那时也常常去江边游玩,秋涛路与钱塘江之间那时还有多条遗存的沙土堤坝,如果抄近路走,还需要翻越这些土坝的。 后来也在环城东路贴沙河边居住一段时间,也常常去河边散步(贴沙河肯定也是塘河遗址)。 这一切总感觉又很多相似之处。 (也是巧合,在家乡居住的地方就是原有海堤的旧址;到杭州第一个居住的地方,也是原有堤坝的旧址边;而此后又多次在杭城其他的“塘河”边工作、居住过)。 ——也正是这样的经历和认识,自然而然地萌发出这样的猜想,推演出解释这种猜想的“理论”假设,也就是所谓的“长直河理论”假设。 对于这样的“长直河理论”,我们反过来逆向分析,应该可以发现,这在工程技术上存在以下这样的科学原理。 1、在滩涂建造堤坝,需要就地取材,必然留有河道。 在工业化之前,人类在海涂建筑和修补堤坝,必然需要就地取材,这样就必然留有河道,而且河道必定很大。否则,堤坝的建造和修补的建筑材料没办法解决。因为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,建筑材料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运输过来,尤其的,滩涂也根本不适合用车船等运载工具运输,只能够就地取材。(这就像现在的远海造岛,不可能从大陆运。) 2、堤坝会消失,但河道会长久保存。 如果建有三、四道堤坝了,此前的就不再有修补的需要;不再修补的堤坝,就会自然流失或者被民众取土而流失。而筑堤取土留下的河道,一般都非常宽大,此后如果没有人去集居,也不会有人填埋;如果有人集居,建筑的房屋就会固化这种格局,同时河道就会被利用而不断加以保护而不会消失。 另一方面,我们都知道,任何工程必定是要“有用”的,这样的“长直河”同样也如此。 它应该不可能是简单的为了农业灌溉,如果灌溉不需要这样长直的河道。 它应该不可能是简单的为了交通运输,如果交通不会是这样平行于海岸线的。 它唯一的可能,就是筑堤修坝(取土后)的遗留产物。 对于“长塘河”,笔者也有特别的感触。 在工业化以前,生产力水平是极其低下的,挖一条河道,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挖掘塘河、修筑海堤,在台州当地俗称“劳塘”,是需要“大军团作战”的,大批劳动力分成每十人左右一组,徒手把泥土堆砌起来,(到八十年代初期才采用“先进技术”,围着架长长的窄窄的滑板梯,一端挖泥、一端队泥,中间流水线运送)用推泥杆把泥块往高堤堆砌。 方法虽然非常简单,但过程极为艰辛。而且,用双手累积起来的纯泥土大坝,会一次次被海浪、台风冲垮、要一次次重新修筑。 除了还有“劳河”,由于“塘河”因为具有交通和灌溉的功能而被不断疏浚,而疏浚的淤泥具有营养而作为土壤肥料,所以,每隔几年,都要组织这样大规模的“劳河”。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每年寒冬农闲时节的“劳塘”、“劳河”依然用这样的原始方法进行着。这样顶着寒风、站在刺骨泥水里绝对无法逃避的“义务劳动”,依然是当地农村最为痛苦的苦役(常有人脚冻伤),也是这一时期的当地学子们拼命学习以求考上大学的最大动力。 在二十多年前,台州沿海尚欠如此艰辛,回看杭州,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地方政府这么可能在市区开凿中河、东河等这么多市内运河?——在农耕社会,这不像现在机械化时代,一拍脑子就可以一个工程。这样浩大的工程,如果不是关乎人类的生存问题,一般地方政府绝对不会去实施的。 ——也正这样的认知和感触,使得笔者第一反应就是不认同“市区之中河、东河均开凿于唐代”观点。 如果从杭州地图上看“从少年宫迤南直至云居山”走向,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西湖东岸。如果“(海塘堤坝遗址大致)从少年宫迤南直至云居山”是事实,那它的“塘河”在哪里?否则其造堤坝的建筑材料从何而来?总不会到西湖中挖泥吧,而塘道是没有这个问题,是可以分段断流挖泥的。 ——也正是对于台州围塘工程的这样认知,使得笔者无法认同“(海塘堤坝遗址大致)从少年宫迤南直至云居山”观点。 总之,家乡台州的一条条大河大坝,杭州的一条条大河大坝,给了笔者这样的认知、感悟和启迪。 同样的,两地这样的地理环境的现实,也应该事实可以证明这一“理论”是正确的。 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jinsihouz.com/hzxpsj/171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2017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杭州市高三年级检
- 下一篇文章: 2017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杭州市高三年级检